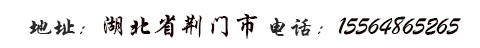从医案辨析针灸诊疗思想
|
岗卫娟,青年中医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医案辨析王执中针灸诊疗思想摘要 通过分析王执中医案以探讨其针灸诊疗思想,主要体现为诊断时重视运用按诊法以找寻受病处,受病处多为相应脏腑的背俞穴、病证局部或经验穴;治疗过程中,选穴一方面重视受病处的选取,另一方面重视类证腧穴相应,同时强调辨别疾病本质如先病后病、病位及新病久病等因素,随证治之。 《针灸资生经》[1](以下引用同此)是南宋医家王执中在汇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前代医籍基础上,参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类编而成,既博引典籍方书与腧穴专书、整理前人经验,又重视临床实践,总结自己临证心得,记载了大量针灸医案,是一部针灸临床名著。所载医案一部分是对古代针灸医家治验的总结,而更多的则是王执中本人进行针灸医疗实践的真实记录。书中共载针灸医案80多则,涉及近50种病证,其中医案40余则。通过对这些医案的整理与分析,探讨其针灸诊疗思想,以资启示当下。 1类证腧穴相应 类证腧穴相应,即某类(种)病证(症)选取某特定腧穴,亦可称为治疗特定疾病的特定穴,即是现代的经验选穴。王执中在医案后多以“凡……必(宜)……”的形式标示其治验,即凡出现某种病证必灸(刺)某穴。这种病证可能是一类疾病,如精神情志病多取百会,也可能是某一症状如脐疼、灸神阙等。 关于一类疾病,如不明原因的神志病,包括不明原因引起的情志异常常取百会穴。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卷四虽从《千金要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太平圣惠方》等医籍中辑录大量治疗精神情志疾病的腧穴方,但在其医案中则不采用这类腧穴方,而是多取用百会穴或以百会穴为主穴进行治疗,详见下列几则医案: (1)予旧患心气,凡思虑过多,心下怔忪,或至自悲感慨,必灸百会。则以百会有治无心力,忘前失后证故也(兼服镇心丹)(《针灸资生经·卷四·心气》); (2)执中母氏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会而愈。执中凡遇忧愁凄怆,亦必灸此。有此疾者,不可不之信也(《针灸资生经·卷四·心忧悲》); (3)有士人妄语异常,且欲打人,病数月矣。予意其是心疾,为灸百会。百会治心疾故也。又疑是鬼邪,用秦承祖灸鬼邪法,并两手大拇指,用软帛绳急缚定,当肉甲相接处灸七壮,四处皆著火,而后愈(《针灸资生经·卷四·癫狂》); (4)有人患痫疾,发则僵仆在地,久之方苏。予意其用心所致,为灸百会。又疑是痰厥致僵仆,为灸中管,其疾稍减,未除根也。后阅《脉诀》后通真子有爱养小儿,谨护风池之说。人来觅灸痫疾,必为之按风池穴,皆应手酸疼,使灸之而愈(《针灸资生经·卷四·癫疾》); (5)舍弟登山,为雨所搏。一夕气闷几不救,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予疑其心悲,为刺百会不效,按其肺俞,云其疼如锥刺。以火针微刺之即愈。因此与人治哮喘,只谬肺俞,不谬他穴。惟按肺俞不疼酸者,然后点其他穴云(《针灸资生经·卷四·喘》)。 上述5则医案中均用百会穴治疗,所治疾病虽症状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均属于心神疾病,症状分别为: ①心下怔忪,或至自悲感慨(心气); ②忽泣涕不可禁; ③妄语异常,且欲打人(癫狂); ④发则僵仆在地,久之方苏(痫疾); ⑤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喘)。 通过分析上述5种病症发现,共同特征是均表现为精神情志异常,王执中认为心主神,故这些精神情志类疾病均与心神有关,属于“心疾”或“用心”(用心过度)所致。后3则医案中,虽用百会治疗后疾病未愈,而是取用其他腧穴治愈。但王执中认为,这些精神情志异常是由于心疾或用心所致,故均首选百会,可以说这是王执中治疗心疾所致神志异常的主导选穴思想。在此,暂且将这种病证取穴方式名为“心神病证取百会”,即无论疾病表现为什么症状(如上述5则医案中提及的心下怔忪,自悲感慨,忽泣涕不可禁,妄语异常,且欲打人(癫狂),僵仆在地,久之方苏,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喘)等),症状表现各异,但其本质只要属于心神异常病证,均选取百会穴,形式类似于“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等四总穴歌的归纳方式,四总穴歌强调的是病变部位与腧穴的对应关系,而“心神病证取百会”强调的是病证类属与腧穴的对应关系,暂称之为“类证腧穴相应”。另卷七“赤白带医案”中,虽取带脉穴而取效,但王执中认为如再灸百会效果更佳,因为“此疾多因用心使然故也”,这也是他“心神疾病取百会”类证腧穴相应思想的又一明证。黄龙祥[2]研究认为,“腧穴主治的表述,其主要模式应该是以特定部位概括,或者在所概括的‘部位’下列举最成熟、最常用的病证……其次是用‘热病’、‘水病’、‘风病’这类类属病证概括”,王执中对于这种心神病证取用百会的思想当属于后者。 笔者对《针灸资生经》卷三至卷七中所有提及百会穴的条目进行了统计(医案除外),其中共有51条,涉及病证有脱肛、汗出而呕痉、唾沫、吃食无味、疟、少心力、忘前失后、心神恍惚、中风心烦、惊悸健忘、小儿惊啼、多哭、癫、痫、狂、角弓反张、中风、尸厥、耳鸣、耳聋、耳痛、头目痛、头鼻塞等20余种,然而在王执中的40余则医案中,取用百会穴的医案即上述5则,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王执中认为百会具有治疗心神病证的作用。通过对古今文献研究,黄龙祥[3]对百会穴适应症提炼总结为头目及心神病证,并在其所附“临床应用举例”中将百会穴适用病证分为心神病证、头痛眩晕、五官病证、中风、小儿病证、妇人病证、脱肛及其他病证共8类。此处总结心神病证与王执中的5则医案及其潜在的“心神病证取百会”类证腧穴相应思想一致。 在上述后3则取百会不效医案中,后分别取它穴而效如:“士人妄语异常”案,王执中认为患者表现为妄语异常且欲打人,“予意其是心疾,为灸百会。百会治心疾故也”。然而却是采用“秦承祖灸鬼邪法”而治愈。“有人患痫疾”案,由于患者表现为“发则僵仆在地,久之方苏”,王执中认为“其用心所致,为灸百会”。然而病未愈,后又疑其是痰厥所致,灸中管(中脘)后疾病稍减。后阅《灸经》发现风池治疗说,王执中按压患者风池发现应手酸疼,故灸风池而愈。“舍弟登山”案,由于症状有“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故其诊断为心悲,采用针刺百会治疗,这正是由于他认为百会穴是治疗精神情志异常的效穴而为。然而针刺百会未愈,由于本病主要表现是气闷,后按肺俞出现压疼,终以火针刺肺俞治愈。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凡出现精神情志症状,王执冲均选取百会穴:“执中凡遇忧愁凄怆,亦必灸此。有此疾者,不可不之信也”,“百会治心疾故也”,这说明王执中认为出现精神情志疾病或用心所致精神情志异常必选百会。后3则医案先取百会穴均未取效,由于精神情志均非主症,而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一种兼症。由此看来,针对病证取穴要辨准病证本质(详见下“重视病本,随证治之”)。 在王执中医案中,类似“凡……必(宜)”的描述很多,如 “凡脑冷者宜灸此”(卷一·囟会), “凡脾疼不可忍,饮食全不进者,皆宜灸”(卷一·中脘), “凡遇忧愁凄怆,亦必灸此”(卷四·心忧悲), “凡脑痛、脑旋、脑泻,先宜灸囟会,而强间等穴,盖其次也”(卷六·脑痛), “凡脐疼者,宜灸神阙”(卷五·脐痛), “凡治脚肿,当先三里而后阳跷等穴可也”(卷五·脚肿), “予因此灸肠风,皆除根”(卷三·便血), “与人治哮喘,只谬肺俞,不谬他穴”(卷四·喘)等等。 以上这类描述反映了其针灸治病选穴的主导思想,暂且名之为“类证腧穴相应”选穴法。 2重视病本,随证治之 如上所述,王执中重视类证腧穴相应,类证并非指症状而是疾病本质,强调“随证治之”,证变治亦变。此处类证所表达的概念,并非现代中医通常认为的证型,而是表达疾病本质的某些因素,如先病后病、病位、兼症、病程长短、病机等,主要含义即并非相同症状即取相同腧穴与治法,而应根据表达疾病本质因素的不同而治疗(包括治法、选穴等)有所不同。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针灸治疗时的一个困惑:一个腧穴主治许多不同症状,同一症状又见于许多不同腧穴主治,以致治疗选穴时无所适从。 依据先病后病而选用不同腧穴:卷五“肩背酸痛”病症下,王执中先列举历代医籍中治疗肩背疼痛等病症相关的内容条文,后附以其医案:“肩背酸疼,诸家针灸之详矣,当随病证针灸之。或背上先疼,遂引肩上疼者,乃是膏肓为患。《千金》、《外台》故云:‘按之,自觉牵引于肩中是也’,当灸膏肓俞,则肩背自不疼矣。予尝肩背痛,已灸膏肓,肩痛犹未已,遂灸肩井三壮,而愈。以此知虽灸膏肓,而他处亦不可不灸云。”此处,本人医案之前,他先引述《千金》、《外台》中以膏肓穴治疗肩背酸疼,然而在其医案中先用膏肓穴治疗无效,继而又用肩井穴而取效。由于其医案与历代医籍所载及《千金》、《外台》所载不完全相符,故其明确提出“肩背酸疼,诸家针灸之详矣,当随病证针灸之……以此知虽灸膏肓,而他处亦不可不灸云”,认为病证虽都表现为肩背酸疼,但要根据具体病症不同本质而选用不同治疗方法。 根据病程新久而选用不同治法,即新病多针,久病多灸。王执中虽非常重视灸法,但他仍认为初病不宜使用灸法。如“久嗽最宜灸膏肓穴,其次则宜灸肺俞等穴。各随证治之,若暴嗽则不必灸也。有男子忽气出不绝声,病数日矣。以手按其膻中穴而应,微以冷针频频刺之而愈。初不之灸,何其神也(《针灸资生经·卷四·咳嗽》)。”“舍弟腰疼,出入甚艰。予用火针微微频刺肾俞,则行履如故,初不灸也(《针灸资生经·卷五·腰痛》)。”“执中母氏常久病,夏中脚忽肿。旧传夏不理足,不敢着艾。谩以针置火中令热,于三里穴刺之,微见血。凡数次,其肿如失去(《针灸资生经·卷五·脚肿》)。” 依据病机不同而选用不同腧穴,如卷五2则“腰痛”案: ①“舍弟腰疼,出入甚艰。予用火针微微频刺肾俞,则行履如故,初不灸也”; ②“屡有人腰背伛偻来觅点灸,予意其是筋病使然,为点阳陵泉令归灸即愈。筋会阳陵泉也”。 上述2例同为腰痛,而分别选用肾俞和阳陵泉治愈。此处王执中虽未明确其诊病依据,即为何“舍弟腰痛案”选用肾俞,而“有人腰背伛偻案”选用阳陵泉,但在“有人腰背伛偻案”中指出的是由于筋病所致:“予意其是筋病使然”,故取筋会阳陵泉。其后,还明确提出“腰疼又不可专泥肾俞,不灸其他穴也”,这表明同一症状并非选取相同腧穴,而要根据不同病机而选用不同腧穴。 3重视“受病处” 受病处王执中明言为“按其穴酸疼即是受病处”,实即传统针灸所谓的阿是穴,现代所谓的疾病反应点,无论从诊断方法、治疗选穴及取穴,均很重视受病处。从诊断的角度,重视按诊法的应用,通过按诊法找寻压痛点以确认病位所在;从治疗的角度,重视选取受病处;从取穴的角度,重视寻找“受病处”压痛点具体所在部位:“须按其穴疼痛处灸之,方效”。王执中还在《针灸资生经》卷二特设“针灸受病处”专篇加以说明,惜已亡佚。 王执中在其40余则医案中,有10余则均选取受病处。通过按诊法找寻病位所在,继而选取受病处作为施术部位,如卷四“舍弟登山”案中:“舍弟登山,为雨所搏。一夕气闷几不救,见昆季必泣,有欲别之意。予疑其心悲,为刺百会不效,按其肺俞,云其疼如锥刺。以火针微刺之即愈。因此与人治哮喘,只谬肺俞,不谬他穴。惟按肺俞不疼酸者,然后点其他穴云。”在卷三“便血”医案中,他甚至认为按其酸疼方可,不疼则不可,选取受病处是治疗取效的关键所在:“予尝用此灸人肠风,皆除根本,神效无比。然亦须按其骨突处酸疼方灸之,不疼则不灸也。”类似医案还有痫疾在风池穴有压痛,梦遗在肾俞有压痛,肠痛在大肠俞有压痛,咳嗽在膻中有压痛等。以上所述压痛点均为经穴,另还有选取疼痛局部作为施术部位即阿是穴:“予尝于膏肓之侧,去脊骨四寸半,隐隐微疼,按之则疼甚。谩以小艾灸三壮,即不疼。它日复连肩上疼,却灸肩疼处愈。方知《千金方》阿是穴犹信云(《针灸资生经·卷五·背痛》)。” “受病处”除表现为压痛点外,还可表现为局部其他症状,如王执中“出冷汗”一案,由于在其膏肓穴处出冷汗,故而灸膏肓穴而愈:“予每遇热,膏肓穴所在多出冷汗,数年矣,因灸而愈”(《针灸资生经·卷五·背痛》)。 综上,从部位来看,受病处既可是腧穴亦可是局部部位,从反应点表现来看,既可是压痛点亦可是异常反应点。受病处与疾病的关系,多表现为相应脏腑的背俞穴、病证局部或经验穴。 4小结 《针灸资生经》卷三至卷七是本书的主体内容,除其医案外,均为辑录前代医籍内容,是将相似内容以病证为纲分类相从。因此,本文从王执中医案着手,分析其诊疗思想。通过分析发现,其诊疗思想主要体现为诊断时,重视运用按诊法以找寻受病处,受病处多为相应脏腑的背俞穴、病症局部或经验穴;治疗过程中,选穴一方面重视受病处的选取,另一方面重视类证腧穴相应,同时强调辨别疾病本质如先病后病、病位及新病久病等因素,随证治之。 参考文献[1]王执中,王宗欣,黄龙祥校注.针灸资生经[M].//黄龙祥.针灸名著集成.北京:华夏出版社,:. [2]黄龙祥,黄幼民.针灸腧穴通考(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52. [3]黄龙祥,黄幼民.针灸腧穴通考(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原载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年11月第19卷第11期 从医案看赵辑庵针灸学术思想 摘要本文通过对赵辑庵医案及主要著作分析,发现其作为民国早期针灸医家,受西医影响较少。针灸治疗时强调辨证(症),认为辨证准确是治疗的首要因素,临证时多采摭《内经》之说,效仿仲景六经辨证;强调辨经选穴、辨性定法,用针用药理相通;重视针刺补泻操作手法,认为行针是对一腧穴实施手法完毕出针后才针刺另一腧穴,与现代通行进针后迟久出针的方法不同;针灸验案记载详明,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包括脉象),诊断病症归经,选穴、具体的针刺补泻手法或灸法,或服药,疾病转归,及误治等,可谓是现代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雏形。 1赵辑庵与《针灸验案》赵辑庵(—),名赵熙,号遁仙。清末民初医家,因疗效显著而闻名山西,被誉为“三晋名医”,尤善针灸。年,北洋政府欲取消中医,中医面临淹没的危险。为使中医不致湮灭,他编撰《针灸传真》八卷,在孙秉彝(当时驻防于雁门关的骑兵团长)支持下,于年由山西代县石印局出版。他以后还陆续编写许多医学笔记及秘方、单方等,这些资料手稿均记在《夏屋山房笔记》,又称《夏屋山房医学丛书》,因民国期间战乱纷繁,未及出版,而毁于战乱。其中关于针灸的《针灸要诀》、《按摩十法》、《针灸验案》及《针灸经穴图表》四卷内容,几经转移得以保留,后由其女赵玉青(彩蓝)于年将四卷集为一册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名为《针灸要诀与按摩十法》。这样,他的《针灸验案》才得以流传。 在《针灸验案》专设“凡例”一节,以说明记载医案的目的、原则、体例,以方便读者。该书是赵辑庵从数十年针灸治疗取效难以数计的病例中,每症各举二三例,每案皆记述详细,证据真切,是其心得经验的结晶,“是书本数十年心得经验,皆有真切证据,取效后始敢立论”,“是书所列各病,系历年针灸经过取效者,虽同病同刺,难以数计,然每症各举二三例,亦足为辨经取穴之用。”该书共记载则医案,包括赵辑庵51种病症80则医案,其三弟赵杰医案8则,其女赵玉青医案11则,其子赵继周医案5则。 该书每案均记载详细,以方便初学者学习之用,这也是赵辑庵编辑的目的之一。他强调:“是书所针沉疴痼疾,并著明取何经,刺何穴,用补用泻,手法分明,且并叙针过几次,灸过几次,初效若何,继效若何,终效又若何,次序不乱,最便初学。”此外,他还记录病因为何、病在何经何脏,不仅有助于初学者学习之用,还可以借此了解他的诊疗思路和方法。 2强调辨证(诊病),尊崇岐黄仲景赵辑庵在针灸验案中,常强调辨证(诊病)准确,则取穴少且疗效迅速,往往取一穴、两穴而出针或针未出即愈者很多。如张泾川头痛案,“每发头顶如锥刺,连及前额,不住以手重按痛处,一松手则更甚……此症是督脉、太阳结邪所致……先取足上两昆仑,及顶后风府一穴,而大泻之,出针痛止。”该书中类似医案很多,不仅赵辑庵医案如此,其女、其弟、其子医案如此者亦有。 若辨证不准,则疾病难以痊愈,即使当时缓解,也会再复发。如在他自己头痛医案中,由于疼痛部位在耳下颊车,眼下四白穴处,用针泻瞳子髎、大迎,疼痛略减,短时而又复发。又用三棱针刺疼痛局部的颊车、头维、下关、角孙出血,疼痛减轻,然而过时又再发。后通过触诊,发现邪结于天枢穴,用针泻天枢穴,针刺后疼痛立止,头部也觉清爽。另如在其牙痛一案中,初以为风寒所致,服用疏风散寒之剂未效,后又针下关、颊车、大迎诸穴,痛稍减短时又复发,后明确为血毒蕴结天枢穴所致,经针泻天枢穴而牙痛愈。由此,只有辨证(症)准确,才能痊愈。 在其医论中,赵辑庵也首先强调辨证诊病对于治疗的重要性,并认为辨证准确是针灸取效的先决因素,“针灸难,认病尤难”、“认穴不难,辨病难……同一病也,而寒热不同,虚实不同,在阴在阳不同。在表在里不同。”他在其《针灸传真》卷一专设“辨症”一篇,并作为开篇“滥传针灸之罪”后第二篇,可见他对辨证诊断的重视。 辨证(症)诊断,他认为必须先要研习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推崇其六经辨证。在《针灸传真·辨症》中提出“欲认病,先读岐黄仲景等书。未有不读岐黄仲景等书,而见病能辨寒热虚实者。亦未有不辨寒热虚实,而施针灸能收效验者。……不读是书者,不可与言针灸。”虽然《伤寒论》、《金匮要略》重在方剂,而对于针灸涉及较少,然而,他认为针灸治病之理与方药通,“汉之仲景《伤寒》、《金匮》,虽详于汤液,略于针灸,而辨证立方,知药石之所治者,则知针灸之所施。” 在验案中,他多遵《内经》、《伤寒》,如张志儒鼻渊案,经十余医医治无效,前医多用散头部风寒、或清肺中火热的方法,然赵辑庵则据《内经》“胆移热于脑,而为鼻渊”的记载,而取胆经风池、胆募辄筋、肝经期门及服龙胆泻肝汤以清泻肝胆经,而治愈七八年之久的鼻渊。再如庆华迎风流泪案,据《内经》补天柱治疗记载,知是太阳经虚所致,故采用补天柱及昆仑而治愈。如在伤寒验案中,他指出“伤寒种类不一,而针刺者亦各别,仲景《伤寒论》分辨六经,针灸家亦辨六经”。 3辨经选穴,辨性定法,用针用药理相通赵辑庵针灸治病强调辨经选穴、辨性定法,用针用药理相通。 辨经选穴,即是通过辨病变所属经脉或所属脏腑选相应经脉腧穴或脏腑俞募穴等; 辨性定法,即是通过辨别病症的寒热虚实属性以确定补泻手法或灸法; 用针用药理相通,即针灸治病与药物治病医理相通,当补则补,当泻则泻,当调脏腑则调脏腑,在其针灸治病的论述中往往比附中药,在医案中也多针药并用。 在其验案中,多明确写明病症所属经脉或脏腑,再据此选穴,如他治疗六例头痛症案: 张泾川头痛案辨为“督脉、太阳结邪”,选取太阳经两昆仑及督脉风府; 程秀英偏头痛案辨为“少阳胆经伏邪”,选取两风池穴; 王玉兰头痛案辨为“肝气郁结”,选取肝经期门及胆经风池穴; 赵辑庵自己头痛案辨为“血结天枢”,则针刺天枢穴而愈; 黄五娃头痛头晕及李三串头痛如锥刺案,均通过三棱针刺头上五行几穴出血而愈,这2例主要由于火邪上冲或瘀血所致。针对这种情况,赵辑庵在《针灸传真》特撰文“刺头上五行各穴出血之经验”,论述用三棱针刺头上五行包括督脉、手足阳明、手足太阳、手足少阳7条经脉所属腧穴出血,以治疗“头晕、头痛、眼眩、眼痛、耳鸣、耳痛、面肿、面痛及一切火邪上冲头面之症”,并指出根据病情轻重决定腧穴数量,不必针刺所列举所有腧穴。 在其医案中,还以“鼻渊刺法宜取胆经”、“牙疼症宜辨经别穴泻气散风出血”及“咽喉肿痛宜分经辨穴”作为医案标题,以突出辨经选穴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性。其他医案标题虽未明确辨经选穴,但也多是先辨经再选穴,在此不一一举例。病症诊断明确、辨经选穴后,便是补泻手法的确定。赵辑庵在其医案中,对每个腧穴的补泻均记述明确,或补,或泻,或灸,或刺出血。 对于因邪气所致的实证,多采用针刺泻法,如张泾川因外感所得头痛,用“大泻之”;王玉兰肝气郁结所致头痛也用泻法;痰气隔胸上下不通一案中,因痰涎壅聚胃脘,气结在胸,属于邪气结聚之实证,故针用泻法,“先泻中脘,行六阴数,又继针两肺俞,泻法如前,后又针泻两天枢,先搓转,后继提插,出针时,又使白虎摇头之法,以泄针孔穴下之邪”,且对于补泻手法的操作描述详明。 对于迎风流泪一案,诊断为太阳经阳虚,用补法,并详细描述补法操作过程,“行九阳数,补其不足,出针后,急以手指揉闭其穴眼”;又如王植卿之父半身不遂案,诊断为本病是由中气不足所致,故针用补法,同时用灸法,“补气海一穴,以益生气之根,先行搓转,继用紧按慢提手法,从卫取气置入营分,手法毕,各灸十四壮。略停片刻,又为之补左腿绝骨穴,以益髓气,补右腿阳陵泉,以益筋气,又补右腿之三里一穴,以益胃气”。先确定病证虚实寒热,再选择补泻手法,病证虚实寒热属性是判定手法的依据。 一般来看,针灸多注重部位和经络辨证,而较少涉及脏腑,然而赵辑庵则认为用针与用药理相通,与脏腑相关者亦从脏腑论治。如尹福羊痢疾一案,初针中脘、天枢(双)、三阴交(双)5穴,以调和胃肠,清肝脾肾之邪,以为可以痊愈,然而患者仅腹痛减,次数减少,而里急后重、红白如故。至此,赵辑庵认识到是由于肺气下迫,肝气郁而不疏所致,用药治疗痢疾以“调和肝气,清理肺气”为主,用针之理与用药相通,所以用针亦然,故又针泻章门,该穴属肝经,又是脾之募穴,以疏肝醒脾,泻肺俞以清手太阴邪气,又泻巨虚、足三里,解肠胃之郁结而愈。选取章门及肺俞是针对肝气郁结而致里急后重,他在《针灸传真·刺痢疾》卷二论述“刺痢疾”篇中,指出“治痢疾者,未有不兼调肺肝而能治愈者。”这不仅体现了用针用药理相通,也体现了他治病首重辨症(病)的思想,只有辨证(症)准确,才能治疗正确。 4重视手法,辟常人行针留针之谬赵辑庵在其验案中,对于手法操作的记述,多是先刺某穴,行某手法,出针,再刺某穴,行某手法,如李智黄疸病“先取巨阙、两内关,大泻之,始行搓转手法,继施提插手法,终又以白虎摇头之法,出针以泻其气,手法毕,又泻两章门……手法如前”等,是对一腧穴实施手法完毕出针后才针刺另一腧穴,与现代通行的针刺方法不同,现代多针刺所有腧穴后,留针一定时间后再一起出针,间或捻转针柄一两次。 赵辑庵在《针灸传真》卷一设“辟市医行针之谬”专篇,论述何为行针及市医行针之谬。他认为“行者,往来不息,即不住循按,不住搓转,未有手不动而针自行之理,亦未有针不动而气自行之法”,行针,即是行针者手不离针,针不离手,以手行针,以针行气,行针完毕后才出针。何时为行针完毕而出针呢?他认为对于由邪气引起病症,以邪退作为出针的时机,“泻法也,针未松而邪未退,不能离穴”,形象地与气筒抽气类比,“欲泻其气者,如用抽气筒抽气,不住抽压,则筒乃成空,停手不抽,而求其气空,有是理乎?”;对于气不足病症,他认为以气足作为出针时机,“补法也,寒未热而气未足,不能停手”,形象地与洒水浇田类比,“欲补其气者,如撒水浇田,不住撒浇,则田乃尽溉而畦四满。停手不撒,而求田畦满,又有是理乎?” 他认为市医插针之后不行针而迟久出针,无异于“身被荆棘刺入,徒伤好肉,而无益病邪”,认为市医误解行针本意,“市医误解行针之意,则误用行针之法,尝见其每针一病,于进针落穴后,将针直插穴内,诫病者勿稍移动,己则移坐旁边,饮茶吸烟,迟久,将针柄略转三两次,或以指头轻弹数下,又照前离开,问其何意,则云‘补泻也’,‘弹努也’,甚或早插一针,晚乃取出,其无理非法之行,实有令人不解者。……市医之插针不动,迟久出针,非行也,欺人之术也,谬之甚矣。 5辨证论治诊疗模式雏形初具赵辑庵认为以药治疗是按病立方,以针刺之,是辨经取穴。民国之前,针灸治疗文献较少,腧穴文献较多,即使《针灸资生经》、《针灸大成》等针灸医籍专列有病证治疗选穴篇章,也记载较略,且据黄龙祥考证,这些篇章也是由腧穴主治转换而来。赵辑庵在其验案中,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包括脉象),诊断病症归经,选穴、具体的针刺补泻手法或灸法,或服药,疾病转归,及误治等,可谓是现代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雏形。 赵辑庵不仅在针灸验案记载中体现其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在《针灸传真》卷二各疾病治疗篇也多有体现。如他在“刺伤寒”篇认为不必拘泥以往针灸诸书记载,临症时辨证取穴定法,“临症行针时,辨脉色,审病情,知六气标本之所在,行先后主客补泻之针法,不必废针灸诸书所举之穴,亦不必泥针灸诸书所举之穴,对症施针,按经取穴,宜补即补,宜泻即泻,何穴可以出其血,何穴可以用行针,不泥法而法自存”。 在“刺痢疾”篇,更明确指出《针灸大成》引《神应经》治病选穴欠详明,未分经施刺,为学者造成困扰,造成单用针灸不能治疗痢疾的错误认识。鉴于此,他将不同类型痢疾根据症状体征,分为不同类别,分别选用不同腧穴和刺灸方法,并比附方药,如“系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服药宜通脉四逆汤,用针则宜取腹上气海、天枢及三阴交等穴,用平补平泻法,以调和其气。针后各灸十数壮,则寒退而阳回,痢疾自愈。”此处他虽未明确提出辨证论治或辨证分型论治的概念,亦未象后世针灸医籍单独列出每种病症的病因、病机、症状、选穴、刺灸法及方义项,但已描述相关内容,如“下利清谷……汗出而厥”、“热痢下重”、“脓多无血”、“下痢脉滑或心下坚者”、“下痢后腹胀满,身体疼痛”等属于症状,“因宿食而致痢”、“有燥屎”、“外感内伤”等属于病因,“里寒外热”、“责在水分”、“责在血分”等属于病机,“宜取腹上气海、天枢及三阴交”、“宜取肺经、膀胱经穴”等属于辨经选穴,“多灸以温其里,再取风池、风府等穴,以通其表,则表里兼治”等属于方义。赵辑庵这种分类治疗及其内容所涉各方面,与现代针灸治疗学教材类似,已初具现代分型辨证论治的雏形。 综上可见,作为民国早期针灸医家,赵辑庵受西医影响较少。针灸治疗时强调辨证(症),认为辨证准确是治疗的首要因素,临证时多采摭《内经》之说,效仿仲景六经辨证;强调辨经选穴、辨性定法,用针用药理相通;重视针刺补泻操作手法,认为行针是对一腧穴实施手法完毕出针后才针刺另一腧穴,与现代通行进针后迟久出针的方法不同;针灸验案记载详明,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包括脉象),诊断病症归经,选穴、具体的针刺补泻手法或灸法,或服药,疾病转归,及误治等,再现其完整的针灸诊疗程序及思想,可谓是现代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雏形。 原载于《上海针灸杂志》年9月第31卷第9期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文中内容为转载,所涉及到各类药方、验方等仅供参考学习,不能作为处方,请勿盲目试用,本平台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期待您的原创投稿,邮箱: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yp/4782.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医方剂学每日一汤酸枣仁汤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