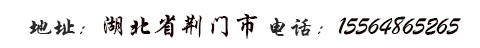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
|
北京治疗最好白癜风权威医院 http://m.39.net/pf/bdfyy/?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作者:李薇薇目录 1.运动了 2.牛棚里 3.逍遥吧 4.扒书架 5.疯跑吧 6.填肚皮 7.学女红 8.叹流年 1.运动了 我得知要搞文革的消息,比许多同龄人都早。 一九六六年初春,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一大早就兴奋地打开一卷照片让我妈看:“会议闭幕那天,周总理接见了我们。看,我就站在总理后面第三排。” 他又指着坐在第一排的两个人:“这是孟启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这是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他翻译的。” 我正坐在一旁,细细品着老爸带回的“义利”面包。我是头回吃这洋玩意儿,就像猪八戒吃到了人参果。听他提到自己正在读的书,连忙凑过去看。 爸爸接着说:“总理在讲话中提到,国家马上又要搞运动了。” “哎!这回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老妈发出一声长叹。 “啥是运动啊?”我问。 “运动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 “那不都是整坏人吗?有啥可倒霉的。”我漫不经心接了一句。 我妈脸色开始变得凝重:“小孩儿家知道个啥!哪次搞运动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就咱家后排住的二妮儿,‘三反’时说她爸贪污,被人对着胸口一拳打多远,对面的人再原样怼回来。两个人像打球一样推来挡去,差点儿没被打死。” 我听得汗毛开始一根根竖起。二妮儿两口都是我妈他们厂的工人,她爱人剪了个偏分头,下垂的头发老爱遮眼睛,走几步就要甩一下。后来这习惯成了怪癖,院里一群小屁孩儿就悄悄跟在后面模仿。我扎着两根麻花辫,咋学都不像。每每笑得肚皮发酸。 运动的到来让人猝不及防。 深夜,我被一阵嘈杂惊醒。迷瞪着睁开眼,看到家里像遭贼洗劫一般:箱子倒扣在地上,书籍四处散落,就连床边的围挡布都被扯了下来。姐姐们满脸惊恐地站在床边,一个女人边推搡她们,边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声呵斥:你们要站稳阶级立场,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 后来我才知道,这女人是个播音员。 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党的喉舌,负责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遍五湖四海。小时候,我就是听着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九评”,才记住了有个国家叫“难死(南斯)拉夫”,也知道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有分歧。但我不明白,这个原本声音甜美的女人,为啥套上个红袖箍,就变得如此歇斯底里。 这帮人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半宿,终于从箱底翻出个存折。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天一亮就去银行冻结“反革命活动经费”,随后呼啸而去。 面对着一片狼藉,我想起不久前和妈妈的对话,才明白那是一个“老运动员”发自内心的恐惧——这次轮到我家“倒霉”了。 窗外露出了一抹亮色,大地开始苏醒。老天总是准时翻篇,从不迟到。可我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往。 恐怖的记忆从这个夏天肇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最高指示成了摧枯拉朽的通行证。造反派假革命之名,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们到处狼奔豕突,抄家、批斗、游街、打人成了随处可见的日常。砸碎旧世界的癫狂,让神州大地陷入到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 被誉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中宣部首当其冲,陆定一和周杨成了走资派和大黑帮。而我爸从北京开会回来,刚刚传达了他们的讲话,这就成了他最初的罪状。 爸爸被关进了“牛棚”,除了审查批斗,还要戴高帽子游街。他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拒不承认这些罪名,一连撕毁了几顶高帽子,又用脚跺得粉碎。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环境下,他的不识时务和“死不悔改”激怒了造反派,被打了一顿后又五花大绑,生拉硬拽到马路上。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一天,我到厂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路过食堂的饭厅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口号。好奇心驱使我趴在玻璃窗上偷看,原来里面正在开批斗会。一个男人站在中间,胸前挂着块一米见方的大钢板,钢板上穿着的两根细铁丝深深勒紧脖子里。那人的脖颈显然无法支撑沉重的钢板,腰被压得几乎弯成了九十度,所以我看不清面容。 待我走到对面换了个角度,看到钢板上竟写着爸爸的名字!我的心顿时缩成了一团,想转身,却觉得腿脚软成了一滩烂泥,只得傻在那儿瑟瑟发抖。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顾不上打水,赶紧低头溜着墙角回到家。 我把看到的这一幕偷偷告诉姐姐,我们提心吊胆地挨到天黑,终于等到了极度疲惫的父母。爸爸被钢板坠得太久,根本直不起腰,进门就躺在床上,竭力压抑着痛苦的呻吟。妈妈哽咽着告诉孩子们,厂里的造反派到上级机关去造反,把爸爸给揪了过来。其间还把她也拽上去陪斗。 我妈出身不好,受爸爸株连,也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每天面对呵斥羞辱,三十多岁就白了头。 那时我十岁出头,弟弟才八岁多,“少年不知愁滋味”。偶尔和小伙伴们打闹嬉戏,被我妈看到就会发出哀怨的长叹:“你爸还关在牛棚里受罪,你们俩还能笑出声!” 笑声都成了对父亲的大不敬。家里终日充斥着忧郁和恐惧,曾经的欢乐和梦想都被埋葬在那个夏天,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中。 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匆匆结束。 2.牛棚里 爸爸被关进牛棚不能回家,妈妈让我去给他送换洗衣服。我心里没抓没落地纠结着:既渴望见到爸爸,又畏惧那天来抄家的凶神恶煞。一路上走三步退两步地踟蹰着,觉得这段路就像一条被拉长的猴皮筋,咋也走不到头。 小屋门口守着哼哈二将。为了防止“牛鬼蛇神”和家属传递消息,我带去的一切都要经过检查:衣服被抖搂开,裤兜甚至衬衣的袖口都被反复揉捏,就连我姐为爸爸烙的两张韭菜鸡蛋馅饼,也被那双腌臜手一层层掀开。查验完,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进去了。 我紧张得浑身冒汗,是因为衣兜里还藏着条“漏网之鱼”,那是妈妈写给爸爸的小纸条。出家门我就偷偷打开看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要多想想孩子们,千万不要走绝路。” 我妈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那段时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除了殒命于棍棒皮带下的冤魂,还时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几天前,隔壁单位又有人从大烟囱上跳下来,把自己摔成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臭狗屎”。而我爸在第一次被游街后就曾说过:“如果他们再这样羞辱我,我就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头撞死。” 显然,这句话成了扎在妈妈心头的一根刺。她就是想得到一句承诺,帮自己拔出这根刺。 来之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长点儿心眼儿,千万别被人发现。抗战时期爸爸就当过地下工作者,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我竟用这种方式接了他老人家的班。 小屋里光线幽暗,“牛鬼蛇神”们趴在桌子两边,正在写交代材料。 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爸爸全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又黑又瘦,手腕上被捆绑的勒痕仍清晰可见。我鼻子一酸,泪水充满眼眶。可想想这不是抹眼泪的地方,又竭力忍了回去。 一位叔叔看到我,问:“这闺女上几年级了?” 爸爸愣怔了片刻,反问我:“你上几年级了?” 那叔叔点着老爸的鼻子:“你这爹当得真不合格,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爸爸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委屈大了,心里说,就是,还爸爸呢!连我上几年级都搞不清!然后撅着嘴回答:“四年级。” 我把衣服和食物递给爸爸,见那叔叔又低下头写东西,才敢把小纸条塞给他。 爸爸快速扫了一眼,小声说:“让你妈放心!我不会走绝路,还等着还我清白呢!” 拿到了这颗定心丸,我总算是不虚此行。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拼缀的全是爸爸的零星往事。我妈在纸条中认定爸爸是好人,我也觉得他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定是被冤枉的。之所以如此“分不清敌我,站不稳立场”,则是凭着孩子的直觉。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书本和电影里的坏人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可我爸不吸烟不喝酒,发了工资就进书店。他除了昏天黑地忙工作,回到家不是抱着本书,就是伏案写东西,从没带我们进过公园,逛过商店。他对孩子的管教,就是督促我们看书学习。父爱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不是儿女情长,更多的是严厉。虽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却从不敢在他面前撒娇。 记得三年级我初学写作文,打完草稿,顺手从桌上撕了张稿纸想誊写一遍,却被爸爸吵了一顿:“这稿纸是我给单位写材料用的,公家的东西你不能用”。 我朝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心想,真是个“抠三儿”,用公家一张纸都大惊小怪!现在想想,这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好同志,咋会是坏人! 再说了,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自然要传达上级领导的讲话。他也不知道中宣部的头头反党反毛主席,因为这就说他是黑帮,还挨斗挨打,我想不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更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大难题。自抄家后,这难题就一直像团麻缠着我,剪不断,理还乱。 一边是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的父亲,另一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该如何选择?我相信爸爸是好人,却绝对不敢质疑光芒万丈的红太阳。 文革让我在懵懂中提前闯入了成人世界,却看不懂这个人人自危,个个发疯的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着石磨的驴,咋也转不出这个怪圈。 3.逍遥吧 摧枯拉朽带来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打倒校长批斗老师后,学校也陷入一片混乱。父母被批斗监管自顾不暇,我们这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小破孩,既不能像红卫兵呼啸街头“破四旧”,也不能当保皇派誓死捍卫某某某,就这样成了没人管教的“弃儿”,被抛在社会上自生自灭。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舞巨手,大串联的红卫兵们穿梭在祖国大地。红宝书发到人手一册,大喇叭里每天吆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走出家门,满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撒得像秋风呼啸时的落叶。每天置身于这种环境,谁又能真正逍遥于运动之外呢! 再说了,自懂事起,我们接受的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所以虽然穿着破衣烂衫,虽然时常饿着肚子,我们依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zz/7339.html
- 上一篇文章: 江阴银渐层猫多少钱一只折耳起司猫多少钱
- 下一篇文章: 不可不知的消防救援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