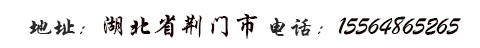跟死亡干一杯,不醉不归
|
“生命纵然异彩纷呈,死亡的终点永远都不曾推移,它安静的等着你,噤若寒蝉。 出生的那一刻,就应该看到死亡的全貌 文/阿新 (一) 这个世界上每年有万人患上癌症,万人难逃死亡的厄运;每8秒钟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毒,每分钟有一名儿童死于艾滋病;每天有名儿童死于仅仅是与腹泻相关的疾病。 这些数字会告诉你病痛和死亡早已稀松平常,我们无力向生命声讨,更没有办法祈求病魔多一份怜悯,能做的只是透过冰冷无情的纱帷,回头去探望逝去的故人,或者讲一讲那些饱经蹉跎的故事。 我有一位学生时代的挚友,父亲患肝病卧床十年,几年前离开了人世,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场无可救药的疾病所能带来的伤痕。我陪他喝了整整一夜,他低着头不断点燃香烟,一杯接一杯往胃里灌酒,嘴上说的轻松:离开也许不是坏事,少了些痛苦折磨。后来酒馆打烊,老板轰我们走,朋友红着眼睛不肯离开,撒着酒疯砸了吧台上各式各样的酒杯,我拉着他逃出酒馆,在马路上一路狂奔不敢回头。 第二天他匆匆办了休学,我不久也离开了那座城市。这些年与他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集,他依旧沉默寡言,偶尔三言两语也多是言不由衷。今年夏天我有幸得以探望他的母亲,她跟我重新讲起那段艰难的时光。我的朋友在休学后患上了自闭症,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内,不肯与人交流,母亲能看到他的时间只有饭点,做好了饭去敲房间门,他并不做声,只是沉默着出来吃一餐饭。 那天母亲照例做好了晚餐,可敲过屋门后许久也不见他的身影,直到她觉察到不同寻常,惊慌失措的找来邻居撬开门锁,我的朋友倒在床头面色惨白,鲜血从他的手腕一直蔓延到红木地砖上,染红了整张床单。 不过这些年他恢复的不错,希望能释怀的七七八八。临走时他母亲对我这么说。 我思索再三,第二天拨通了他的电话。 他说他在家乡的水库边钓鱼,阳光晴好,四周都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我说帮我留些鱼饵,备支鱼竿,来年我也去看看水塘和油菜花。他笑着说你静不下心,鱼儿不喜欢有野心的人。 他说话时平静如水,我能听到田野里的风。他母亲说的没错,时间会把所有都冲刷的七七八八,那个醉酒狂奔的深夜,那个血迹斑斑的黄昏。 (二) 年11月的香港繁华依旧,旺角人声鼎沸,弥顿道华灯初上,几只晚归的渔船泊向避风塘内,维多利亚港夜色撩人,一艘艘豪华游轮出港或者靠岸。 那天的红馆座无虚席,梅艳芳身着长摆婚纱,一袭雪白立在几万人的眼前,她低着头问台下的歌迷:我穿婚纱好看吗?但是我错过了时间,我相信我没机会了。 45天后梅艳芳因子医院病逝,那天是12月30日,距新年只有不到四十八小时。 那年香港SARS肆虐,梅姐为筹集善款发起了《1:99音乐会》,活动结束后她用调侃的语气告诉记者“会生场大病”。同年九月她公开了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在媒体见面会上坚定的说“一定会好起来”。 她孑然一身,最终难违天命。 越是美艳动人,越是敌不过冥冥注定。一场光彩夺目的离开会被人长久流传,可是人去楼空,留得住牵挂,留不住远去的身影。更多的人只是沉默着倒下,入土为安,每年有几包铸钱几束白烛,哔哔啪啪的两串爆竹声响,或者索性洒脱的把骨灰抛向空中,落入江头,等到祝祭祈年的日子,看着亲故在江边撒上一圈白酒,便是所有的热闹。 我常在想,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才够资格够勇气去谈病痛生死。这自古以来都是个肃穆凝重的话题,死亡没有办法经历,所有的感受都源于耳濡目染,你目睹好端端的生命日复一日的苟延残喘,你听闻远方的老友正在和死神博弈,除了感慨生命的阴晴不定,自然也会多一分对生死的理解。我只是揣测,也许死之将至的时候,这种理解会最为深刻。梅姐离世的那个深夜,好友成龙向媒体说了这样一番话:她一生都爱热闹,可她说今晚不想有人高唤她姓名。 她一世喧嚣,等到行将就木,也只是想要一个波澜不惊的结尾。 作家李碧华在《花开有时,梦醒有时》中回忆,最后一段时光里,梅艳芳曾在病榻上读她传真的舞台剧本,医生告知“癌细胞扩散,今后再不能登台演出”,梅艳芳听后抛下一句“既是这样,我便走了”,不久便陷入昏迷,在年终深夜悄然离去。 (三) 浮光掠影几十年,你把悲欢看遍了没。也许你看不到,看不到死神步步逼近张牙舞爪。 可若是一个人得知自己死之将至,会是怎样的心情。这是一个妄自菲薄的问题,但我却时常想要看明白,因为你我总有那一天,或者只是心脏停止跳动的一瞬间。 几年前我读到一本叫《花田半亩》的书,认识了一个叫田维的女大学生,目睹了一场弥留之际直面死亡的反抗。她的出生并没有呱呱坠地,超过预产期五天在腹中没了胎动,医生宣告她的死亡,直到一声微弱的啼哭,她死而复生。她已经死过一次,所以毫不畏惧,她说让我的右眼去流泪吧,另一只眼睛,让她拥有明媚与微笑。田维在自己二十一岁的夏天安静离开,其导师梁晓声说:经常与死神波澜不惊地对视的人,是了不起的。 “让时间忘记我,让季节忘记我,让思念忽略这一切。我汹涌或者平和的情绪,如水如梦。当人即使在梦中,仍不知幸福的所在,那才是最深的悲伤。一路的荒野,我们万水千山。” 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清丽俊美的句子。我与她年纪相仿,对生死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我只是远远观望,而她却深陷泥沼。耐人寻味的是,隔岸观火的我把生死讲的歇斯底里,惘若其中的她反倒看的坦荡明朗。其实生死再如何风轻云淡,也不是稀松平常,我还是想要找到些什么,关于面对死亡的众生相,关于油尽灯枯前的种种牵挂。 年卡夫卡死于肺病,他生前三次解除婚约,只是因为恐惧琐碎的家庭生活会磨灭他赖以创作的孤独,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能如他所愿。 年《黄金时代》拿了“联合报”奖,直到两年之后王小波心脏病突发猝死,书都不曾卖完。他甚至考取了货车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就靠这个吧。” 好莱坞“第一夫人”英格丽·褒曼于年8月29日因乳腺癌病逝伦敦,那天适逢她坠落人间的第六十七年,前夫道拉斯在那天送与她一束鲜花,她忍着病痛与前来探望的宾客举杯共饮,不就她便离开。其骨灰一部分抛向大海,一部分埋在斯德哥尔摩公墓。而在年五月,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刊登自己的文章《我的医疗选择》,宣布为降低乳腺癌风险进行双侧乳腺切除手术,她在文章末尾说到:“生命总是伴随无数挑战,唯有我们承担和掌控挑战,才不会令我们心生恐惧。” 有人死的伟岸,就有人死的卑微,但我一直坚信没有人面对死亡时能毫无畏惧,于生没有眷恋,于死没有动容,便称不上生死了。 如今的田维长眠于北京西山脚下,一个叫温泉的墓园,墓碑前常年摆着一束龙胆花,那是她生前至爱。 (四) 有些事巧合的可怕,在我仓皇写下这些文字之际,突然传来一位旧友坠楼自杀的消息。我们也有三五年不曾谋面,期间有些零散的联络,通话时仍有欢声笑语,我习惯他冷静平和的语气。他生前虽然不多言语,对生活却热情满满,不知是什么让他失去信心,做出这样万念俱灰的决定。 我同某位留学北欧的挚友谈及此事,她说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挫折能让人只求一死,死亡听起来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没有什么比一走了之更加棘手。我向来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足以让我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后来想想看,或许也不尽然。当你站在二十层的楼顶,脚下除了冰冷的空气和看热闹的人群,还有苦不堪言的过去,还有支离破碎的心,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迈出脚一跃而下。 尚存于世,便没有资格评论一场生死。自杀从来都是一桩被冠以浅薄、懦弱的悲剧,我们站在一个锦衣玉食的立场,指责自杀者的冒失冲动,这并不公平。 没死过,怎么知道不至于。 最后我想到芥川龙之介,他迷恋死亡,多次尝试自杀,在他眼里自杀更像是一门行为艺术。他曾为自己设计各种各样自杀的方式,最终选择服用大量安眠药,这种符合他“美学审美”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的人大多都像雷尼尔所描写的一样,理不清自己究竟是为何而自杀吧。我们的行为背后动机也总是复杂的,虽如此,至少现在的我确实是茫然不安、我对我的未来是茫然不安的。” 昭和二年,芥川龙之介写下遗嘱,同年自杀。比起以上摘录,另有一行遗言更耐人寻味,他说“即便我已决定好自杀的方法,心中仍旧有半分是想着活下去的”,面对死亡坦然如他,也尚存继续生活的残念。 看来就算是一心求死,也没有办法了无牵挂。由此我更想得知的是,我那位坠楼的朋友,或者这世上千千万万自杀的亡魂,那一脚踏出去,那一瓶药丸吞下去,或者被绳索勒住脖颈之后,有没有后悔过。 生命纵然异彩纷呈,死亡的终点永远都不曾推移,它安静的等着你,噤若寒蝉。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应该远远地看到它,看到自己身后的结局。死亡的全貌随着生命的演进,一丝一毫变得清晰无比。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一时片刻想送葬自己的念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还不至于付诸实践,却仍会情不自禁就为自己规划处一条向死而生的路径。我们借此把生死翻开,斗胆去窥视它棱角分明的面容,看它怎么把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一语带过,又怎么把一命呜呼的霎那动辄千言。 我那在天堂在远方的故友,那千千万万上天堂下地狱的亡魂,来吧,干一杯,不醉不归。 读者来稿作者介绍 阿新,喜欢太宰治,喜欢描述烟酒姑娘和死亡。 手臂上有文身“beingtowardsdeath”,翻译成汉语是“向死而生”。(反骨) /如果你也想来Gao/ 请戳这里,我等你。 [活着的人要更加精彩,我与你一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yp/7440.html
- 上一篇文章: 耽误姑娘十年青春,又始乱终弃,你良心被狗
- 下一篇文章: 年12生肖最新助运植物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