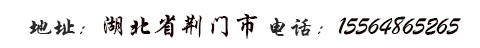ldquo忆满京城情思华夏rdq
|
清明是中华民族祭奠祖先、缅怀先烈、追忆逝者、悼念先人的传统春祭节日,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体现了中华先祖“天、地、人”和谐合一的思想。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节日之一,又值人间四月天,因此广受古今文人墨客的青睐,诞生出无数优秀的诗、书、画作品。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预防疫情传播扩散,营造文明、环保、节俭、安全的良好节日氛围,海淀区文化馆(北馆)开展了“忆满京城情思华夏”清明主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现将征集到的优秀作品进行线上展示。 书法作品 作品:毛笔空心书法 作者:张嘉龙 绘画作品 作品名称:《丰碑》 作者:江涛 摄影作品 作品名称:《颐和园春景》 摄影:席勤 作品名称:《清明的怀念》 摄影:席勤 作品名称:《历史的记忆》 摄影:席勤 作品名称:《江南三月》 摄影:席勤 作品名称:《黑天鹅的一家》 摄影:席勤 诗文作品 《踏歌清明》 黄良杰 (一) 父亲和小爹赶在清明前为爷爷奶奶树了碑,圆坟。 石碑是父亲打听到邻镇专事刻碑的工人定做的,挑了大尺寸的碑,刻完蒙了红布拉到后山来。砌墓的砖、泥沙是谈好价自行用拖拉机运来的,省了四五百块钱的运费。 这是一座庄严的石碑。除了爷爷奶奶的姓名、生卒年份,碑身上还镌刻着他们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以及一众儿媳女婿、孙子孙女儿的大名。我第一次知道大伯、小伯的名字——爷爷奶奶为他们取了比父亲和小爹的还诗意的名字。我的大伯在两个女儿尚幼时生病去世,而我的小伯不到二十岁就因一场如今看起来不那么难瞧的病英年早逝。那是年,我当然没有见过我这位小伯,但是他活在父辈的记忆中。听说小伯聪颖好学,会写好看的毛笔字,甚至考上了高中,“学习成绩好得很”。如若在世的话,兴许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奶奶是在我快上初中那会儿去世的。从此,每到除夕、清明,我都会跟着父亲到奶奶的坟头烧纸磕头。爷爷在时,除夕团圆的午饭,菜上齐了往往先不能吃。爷爷要盛几小碗饭放在桌上,“叫”一下奶奶、小伯。然后大家全部出去,关上堂屋门等几分钟,再开饭。午后,父亲一般会上街买红纸糊的竹竿儿灯,灯底放一个半切的挖开瓤的萝卜,插上蜡烛,放在搁柴禾的小屋里。天快黑的时候插到坟头点亮,叫送灯。元宵节会再送一次。 清明的祭奠则更为声势浩大。油菜花开的时候,蜜蜂在金灿灿的花枝间嗡嗡飞动,一家人相携从田间地头的青埂蜿蜒登山,在坟前给奶奶、大伯、小伯挂上清明吊子,烧黄纸,磕头,放一簇短短的鞭炮。大伯、小伯的墓地往往蒿草横生,没有爸爸的带引,我是找不到路的。祭奠完故人,父亲兄弟姊妹和我们一众小辈往往要一起吃顿饭,清明可以是算是春节过后的一次齐聚。这种我能参加的热热闹闹的清明节或许打我上高中起就很少有。这几年就连春节也都在外萧条地过了。 (二)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温泉墓园,长眠着一个女孩儿,她叫田维。田维的名字知道的人或许不少,但对更多人来说应该很陌生。她有一部著述叫《花田半亩》。 离我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子午书简》栏目听说田维和《花田半亩》的故事已经过去10多年了。那个暑假,我只是一个无知的即将升大三的穷学生。返校后,我就到西单图书大厦找这本《花田半亩》。我真的找到了,蓝白龙胆花封面的厚厚的好几本,似乎是新上架。它被摆放在二层电梯边的青春文学区域,位置虽然不错,可是和一块儿的其他红红绿绿黑黑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格格不入。《花田半亩》是一部有关生死的思考的厚重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一般的青春抒怀的故事或者小说。 《花田半亩》是田维日记的合集。一偏偏文字优美的日记,记述了她的生活,她的病痛,她的思考。日记里有很多隽永美丽的语句,那不是浮华的辞藻堆起来的,而是她的生命赐予的。从她的文字里,我知道了,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文字的人,单纯的人,坚强的人,那么不幸的人。自习备考的日子,我在阶梯教室里做题,累了就翻开《花田半亩》读一读。读着读着会笑,也会心伤。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可田维的文字我读得进去,并且很喜欢。我也曾装模作样地学别人去读张爱玲,到现在连书名都不记得了(我骗你们的,实际上我记得,是《倾城之恋》)。读书这件事情,难道也得看缘分? 田维在病痛中考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上了她最爱的文学专业。我也曾到北语闲逛,多年后碰到一位北语的毕业生,还傻傻地问,你听没听说过你们学校的田维?只不过一切都已随风而逝,青春光景不在,只剩下回忆和茫然。 文稿:周昱宏 审核:岳昌涛 文旅海淀 纵观创新之城,品味人文海淀! 欢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gj/10415.html
- 上一篇文章: 高血压是怎么治疗注意这八大药方
- 下一篇文章: 丨年级丨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