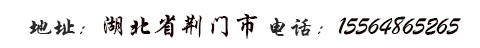我和我的病友们
|
这个夏天,我返老还童了。 印象里,好像是小孩子们感冒咳嗽引发肺炎的,不想我居然也感冒久咳引发肺炎。平生第一次在CT报告单上看到“左肺下叶炎症”的字样,我觉得好专业啊。 现在想来,在孩子们期末考试之前2个周,大概是6月中旬,我就已经有了症状,但一年以来,我习惯了自己的乏力不适,以为吃点药休息休息就好了。我在家里也戴上口罩,以免传染孩子们影响期末考试,甚至不再和孩子们同床,也不再辅导孩子学习。期待着这波感冒行情赶紧过去。但我依据经验服用的猴耳环消炎药、十味龙胆花颗粒、蒲地蓝、板蓝根等并没有阻击成功。 一个周后,我去了单位附近的诊所,大夫开了头孢和肺力咳。可是,感冒的症状消失后,咳嗽却越来越厉害。每天早上,我伏在洗手台前连续咳嗽至少半个小时。走到哪要把纸巾带到哪里,一天要用掉三四包抽纸。有的时候,伏在垃圾桶前不断地咳嗽,要把双手分别放到胸部和腹部,才能咳出成果。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架自动咳嗽的机器,完全不受本人控制,似乎整个嗓子都肿了起来,疼痛难忍,好像有细细的小刀在嗓子里划过一样。在上一场连续的咳嗽和下一场连续咳嗽之间,我懂得了什么是苟延残喘,觉得活得狼狈而没有尊严。因为连续不断地咳,我头痛欲裂,即便从床上走到卫生间,短短十步的距离,也需要扶着墙慢慢行走。我只能请假病休,期待头孢发挥威力。 到6月24日,我觉得头孢已经发挥了数天的威力,似乎咳嗽的次数也变少了,但单位附近诊所的大夫却告诫我,头孢最多吃7天,医院吧。于是下午我去了省中医。大夫给开了中药和十味龙胆花颗粒,并继续吃原来的消炎药。 7月3日,我再次复诊。大夫觉得我的症状不常见,听诊器基本听不到罗音,但我的难受却是实实在在的。咳得次数是有所减少,但感觉咳得很深。大夫建议我做个CT,结果显示为左肺下叶炎症。大夫指着CT片子上的灰色说:炎症区域还不小,住院吧。我经常咳嗽得不得归位的五脏六腑忽然就沉静下来。 我马上入院,并祈祷速速地打上点滴。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挨过下一拨咳嗽了。虽然我一直不喜欢打点滴这件事,但只能臣服了。 在省中医打了一下午的点滴,到了晚上,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在两轮咳嗽之间入睡了,不由得喜上心头。 医院西院肺病科大病房共有6张病床。除了我一个中年女可以生活自理不带看护以外,全是需要家人陪护生活不能自理的老者。靠窗户的兰医院,在抢救室呆了几天后出院没几天,又进了省中医。她经常发烧,没有胃口。老伴70多岁了,早上5点不到就起床从千佛山走到饮虎池,给她买甜沫和牛肉烧饼。一开始,她只能喝点甜沫,后来就可以加个鸡蛋。终于有一天,她又多吃了半个烧饼。大夫查房的时候,老伴很高兴地说:今天放卫星了,多吃个半个烧饼。兰大娘排便困难,大夫让吃萝卜顺气汤。快递小姐姐走了之后,大爷打开汤看了看:哼!十块钱,我能买够吃十顿的萝卜,也加上两颗小白菜,也撒上几个枸杞。然后大爷把外卖的手拎纸袋叠起来:我明天也用这个包着,也找个坤角来送。他说了半天,只收获了老太太的几个白眼。给老太太端了尿盆又端水杯,老头又有话了:我现在就是个端盘子的。老太太嫌弃他,他又有话了:我现在就是老妈妈的尿盆子,光挨呲。老太太不肯吃,他这么劝:你省吧,省多少饭钱也不及药钱。二婶子掉井里了,耳朵挂不住啊。医院食堂的馒头很大,我得很努力才能吃上一个。大爷就说:吃馒头好啊,谁能吃上一个谁就能出院。别人笑话他:你倒是能吃一个,也没出院啊。 再是愁肠百结的日子,也让兰大爷的调侃给镶嵌了金边。 兰大娘旁边的病人大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神志也不太清楚,不时大喊几声:要死了,要死了。刚住院的几天,突然的叫喊常常吓得我心脏漏跳了几拍。他没有牙,护工用一个奶瓶喂他流食维生。 他出院后,再住进这床医院转进来了。医院的,治疗之后,倒要担架抬着转院。他也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70多岁的老伴照顾他,两人吃什么都用粥或开水泡过。他的老伴驼背,人很厚道,一看到我喝水,就要拿起暖瓶给我添。我谢绝了几次只好说了实话:大娘,我是特意少喝水的,一天5瓶针,也不渴,喝水不过是润润嗓子。喝多了带着管子上厕所好麻烦,一只手拉拉锁系扣子很高难度的。 靠着门的大爷非常瘦,两条腿细细的,看起来僵硬而没有生气。他可以扶着人拄着拐棍缓缓行走,哆里哆嗦的。他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谁也不懂的啊啊呀呀。所以,常常听到护工或家人问他:喝水吗?一阵啊啊呀呀。啊,不是,要走走?一阵啊啊呀呀。要起来坐着?一阵啊啊呀呀。越是猜不准,他越是着急,哎哎呀呀的声音越大越急。家人冒着济南高温送来的午饭,他不吃。看护吃完了以后给家属打大哥,早上饭没吃,我吃了。中午也不吃,我吃了。怎么办呢?这位大爷大声喊疼,“啊”的一声直贯云霄,吓得我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护士和大夫们飞快地集合到他的床边,并把门关上。其他病房的病人涌到走廊,互相打听着,我觉得他们好勇敢。这样的叫法,宛若受刑。围观,是找虐,也不甚体贴。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觉得,三个病人也不遑多让。有时候,我宁愿呆在走廊里护士站前的椅子上打针,也不愿意回到病房。无论是病友的呻吟还是喊叫,都让我感觉更加憋闷。我常常想,活得这么狼狈这么努力,若不是有诸多牵绊,病人们宁愿解脱而去吧。我记得我爷爷去世前,就常常给奶奶说:真是遭罪啊,真不想活了。看着孩子,又不舍得。 兰大娘常常表示不想努力了:我先走啊,老头子跟在后头吧。老头还是很幽默:你前面走我后面跟,跟不上就打离婚。 到了这样的年纪,病床前有老伴可以撒娇,真是一种福气。兰大娘的福气不仅于此,读大学的外甥儿天天坐在床边,她还嫌弃孩子不会照顾人。女儿给她剪脚趾甲,她也有意见。 想来是病得太久太辛苦,有这样的家人,兰大娘依然是难以被安慰的。老伴、女儿们、外甥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兰大娘却难得一笑。家人们也常常露出黔驴技穷的无奈。 但查房的臧国栋大夫好像是个例外。 每次来查房,他都是很高兴地跟兰大娘打招呼,好像刚捡了块钱:感觉怎么样啊?摸摸脉、按按肚子,像哄小孩一样问:吃了什么,吃了多少,喝了什么,喝了多少,大便小便如何……。他问谁都问得很详细,病人可以感觉自己是真的被“看到”了。语气也令人愉悦,兰大娘也难得地露出几丝微笑,居然在臧大夫微微弯腰听诊的时候,用手抚了抚臧大夫的头发:有40了吗?都有白头发了,愁得么?愁孙子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藏大夫应该是80后,忽然被调侃操心孙子,略顿之后也笑了起来。兰大娘的外甥儿说:让你这样不好好吃药的病人愁得呗。 兰大娘一提吃饭就说:不想吃,没胃口。她常常拒绝口服药,说:没用啊,吃了也没用。家里人是各种劝慰轮番上阵,藏大夫也总是用哄小孩的语气说:你得好好吃饭,好好吃药。 又有一天,臧大夫查房还是直奔兰大娘,逗她: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兰大娘鼓励大夫说实话。藏大夫说:坏消息是——由于你不好好吃饭,营养跟不上,你要补充蛋白……好消息是——治疗的各项指标都有了好转……兰大娘很明显地松了口气,地道的济南话溜出来了:道理都懂,就是不想吃啊,吃不进去。到了兰大娘住院28天的时候,藏大夫查房又逗她:老太太,快满月了。兰大娘也笑:快满月了。 7月14日,我治疗后的CT结果出来了。在医生办公室的电脑上,臧大夫给我比较治疗前后的肺部:你看,原来是一片,现在是条索状了,好了很多,还要继续吸收。我磨磨蹭蹭地问:病友们都嘱咐我好好治疗,别留下病根了。我这不会形成习惯吧,一感冒就咳,一咳就肺炎……亲戚家小孩就这样。或许是我反复几个问题都是如此,藏大夫看到了问题后的压力,说:我给你看看我的片子吧。 藏大夫从电脑上调出了他去年12月肺炎CT的片子给我看:你看,位置都是一样的。然后给我看了他在3个月之后复查的片子。我很不地道地大笑了:怪不得都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知道你也得了肺炎,我就放心了。全办公室的人都被我如此直白的不地道乐坏了。 我是真的开心了,看到他如此精神饱满极富温度和热情的工作状态,而且是在肺病科这样常年接触肺部疾病患者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肺炎,嗯,真的会成为小case。至少,我没有这么多感染的机会啊。 后来再查房,我就特意找臧大夫问:你治愈后又感冒了吗?是啥症状?大夫们就笑:这是病友之间的交流啦。确实,除了医生专业的治疗意见,我还需要来自病友的经验。可惜整个病区,据说只有一个和我一样病情的病人,我也实在不是跑到别的病房主动结识病友的材料。 后来和臧大夫聊起来,他的一些观点深以为然:病人本来是缺乏关爱的群体。病人一定是对自己缺乏照顾和关爱才生病的。中医讲情志,疾病是和情绪有关的。我们大夫不但要努力治疗病人,还要用我们的正面情绪带动病人打败低落的情绪…… 他的话也令我想起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话做起来其实挺难的。每个病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兰大娘,每天不开心也没胃口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胀总是喘不上气来,只给她用药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各种哄,用笑脸去感染各种愁眉苦脸。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查了一上午床,医生的笑脸会不会余额不足?得把自己活成什么样才能不断输出热忱呢? 事实上,这次住院,令我有这样感受的医护人员有很多。 到病房走廊的开水间接水时,自己举着吊瓶要去取结果时,一位素不相识的物业姐姐总是要给我帮忙,笑容能甜到人心里去。她手脚不停地忙,还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笑得跟花一样,我好佩服她。 在门诊时,我遇到的是陈宪海主任。当时排在我前面的有好几位病人,但他一边给其他病人问诊,一边注意到我的咳嗽,让学生把凳子让给我坐。他的“看见”先于他的医术已经帮助和安慰了我。选择这位专家本来是分诊台护士的随机之举,但我相信有这样“看见”和体贴的大夫,一定仁心妙术。林巧稚让学生们写病历时,唯一得“优”的学生只比其他人多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有豆大的汗珠…… 十多天之后,我带着左手上十几个针眼和一袋子草药、中成药、西药出院了。回家之后,我打开煤气蒸上馒头,用电锅做上粥,然后开始炒一个最简单的菜——丝瓜炒鸡蛋。炒了几下,我发现自己的腿在哆嗦,干脆添点水煮成汤吧。我扶着墙走到沙发前坐下,看着茶几上一堆中药,一瞬间泪如泉涌。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像风一样奔跑在田野上,还毫不客气地把邻居家的小男孩摔了几个跟头。我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敏捷地跨栏,次次都能赚到毛巾牙刷一类的奖品。那个健康快乐强壮能干的我去哪里了? 哭完了,想起了我的病友兰大娘。兰大娘盼望着“满月”回家能洗个澡,被女儿拒绝了:你现在很虚啊,妈,回去得歇歇再洗澡。兰大娘很不高兴地扭了脸。我想起她不高兴的样子,极其不厚道地笑了:兰大娘,你回家就是洗澡,洗到一半也得没力气呢。 乏不乏力,咱说了不算。但笑还是哭,自己倒是可以试试。 由卫娟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用手机发文章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zz/3963.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一药龙胆214
- 下一篇文章: 她出生时死而复生,生命绝唱花田半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