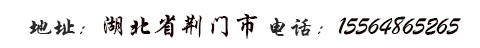钟叔河念楼壁上四则艺术中国
|
罗章龙书自作诗 ——“念楼壁上”之一 钟叔河(长沙) 抽刀断水水长流,语不惊人应便休; 五十年来无限恨,山林朝市各千秋。 罗氏自云此诗作于一九七八年,写成条幅赠我却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此时他已年近九十,但气色仍佳。 一九四八年在长沙,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因家住河西,假日常在湖大阅报室和学生自治会等处留连。有次路遇一位身穿灰呢大衣、戴着黑框眼镜、手拿几册图书的中年人。同行的湖大外文系学生雷君告诉我,此人为经济系教授罗仲言,他和另一位教授李达一样,过去都是共产党。 罗仲言即罗章龙。他比毛泽东小三岁,一九一五年两人以“纵宇一郎”和“二十八划生”的署名结交,随后同组新民学会,同在北京与蔡和森、肖子升等“八个人聚居小屋,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一九二零年北大建党,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李大钊负责领导,张任组织,罗任宣传,毛泽东则回湖南建党。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毛罗同时进入九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五人的中央局。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苏联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硬塞进政治局掌握大权,罗章龙随即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对抗,被政治局宣布开除党籍。他于是进大学教书,成为了经济学教授。 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带着岳麓书社出版的《椿园诗草》到北京去看罗章龙。他已被安排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当顾问,在三道门住上了“部长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主动给我写了这幅字。写的诗却是《椿园诗草》中《炎冰室杂咏》九首之六,我看过了几遍的,于是便笑着问他: “下一首还有两句,‘众口悠悠安足论,吠尧桀犬本寻常’,看来你老人家的牢骚不小呀。还有‘炎冰室’这个斋名,对世态炎凉恐怕也深有感触吧。听说你老早就申请恢复党籍,不愿学李达重新入党,结果并不顺利,是不是啊?” “没得的事,没得的事。”他也笑着,连连摇手。 “你老也不想想,建党党员,三届中委,你老这样的资历,若是恢复了党籍,位置又怎么好摆呢?”我还是笑着问。 “没得的事还要问,你也是湖南骡子,太倔了。” 话虽如此说,他还是满面笑容。“语不惊人应便休”,看来他真是“休”了,一切都放下了,想开了。他一面笑,一面又拿出一本《椿园载记》来送给我。这是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印的,内部发行,乃是他的回忆录,头一节为《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最后一节中又谈到汪精卫误认他为铁路工人,向他表示“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可读性很强。 念楼壁上之二 ——李一氓无题有赠 钟叔河 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 李老(李一氓大我26岁)这幅字,是年4月写了寄来的。上款“无题书奉叔河同志雅鉴”,“无题”即是诗题。 此前不久,他有文《纪念潘汉年同志》,也用这首诗开头,并且解说道:“第一句指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显然这是一首追念亡友之作,虽然声明“并无深意”,其实还是大有深意的。 一九二六到七七年正好“五十春”,五十年来“电闪雷鸣”一直不停,电母不停地烧,雷公不停地打。前二十多年,潘汉年跟在雷公电母左右,烧的打的都是别人;后二十多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烧的打的就是潘汉年小董等“湘灵”“倩女”了。 诗人对此的感受,《纪念潘汉年同志》文中有所说明:“年‘潘杨事件’发生,有好多疑点……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了一些嫌疑……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从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 这番自述,岂不是对“电闪雷鸣五十春”更切实的解说,也就是这首《无题》深意之所在么,但他为何会将它“书奉”给我呢? 我和李老只有过“一面之交”,一次面对面的交谈。那是年3月,他不知从哪里见到几本《走向世界丛书》,便通知我进京开会。会期八天,彼此都忙。某次用餐时,他移樽就我,说有部由缅甸去英国的清人游记刻本相赠。我知道这是王芝的《海客日谭》,因已有复印本,便辞谢了,却急于向他说起曾国藩全集必须重编的道理来。他对于原刻《曾文正公全集》有哪些“不全”也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大约交谈了四十多分钟,连准备送他的一本我在劳改队时油印的《水浒叶子》(因为见过他介绍《明刻陈志莲水浒叶子》的文章)都来不及提,我便在陆续来找他谈“项目”的人快要围成一圈时告退了。 虽然只有这“一面之交”,李老却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文字。9月和11月间,他两次来信,动员我将为《走向世界丛书》各种所写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后来《从东方到西方》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写来了精彩的序言。年3月,《人民日报·大地》发表了我写的《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一个多月后,便收到李老寄来的这首《无题》,这回他却没有另外写信。 李一氓是真正的老革命、老文化人。我还未出世,他就译过《土地问题》等许多书,编过《文化批判》等好些刊物。我六岁时,他就当上新四军和东南局的秘书长。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他则是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他和我之间的距离,实在大得很。 应该说,在很多方面,李一氓和我都是迥然不同的,我和他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某个时候也可能会产生某种共同的理念或感情,比如说,对《水浒叶子》的喜爱、对走向世界的关心……还有电闪雷鸣时的“惊心动魄”,对潘汉年之死的“目眩神伤”…… 图片说明: 1.李一氓书《无题》诗 2.李一氓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信 李锐的三次赠诗 ——念楼壁上之三 钟叔河 今年九十七岁的李锐老,是我一九四九年进报社时的老社长,曾三次写诗相赠,其一云: 依然一个旧魂灵,风雨虽曾几度经。 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 五十知非犹未晚,骨头如故作新兵。 此原是他的五十自寿诗,一九八二年(壬戌)写寄我时,他已经六十又五,“延水洪波”和“庐山飞瀑”早都过去,其本人亦非“新兵”而是中央委员了。 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时我四十八岁,到一九八二年正好年满五十,对于“作新兵”确实不够努力,但读到“依然一个旧魂灵”和“骨头如故”时,想起克伦威尔的名言“PaintmasIam”,仍不禁顿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 赠我的第二首诗《寄叔河老乡》,就是直接对我说话了: 次青并列谢恭维,无奈生平不合时。 幸有言辞飞网上,老夫尚保岁寒姿。 李锐和我都是平江人,次青为平江先贤李元度之字。二零零三年我作文悼念一九三三年苏区肃反错杀的“平江才子”毛简青,文中有云,“平江与江西义宁接壤,两地文风皆盛。平江古有李次青,今有李锐,都是有名的才子,毛简青生于二李之间……”都是如实叙述,并无意恭维也。文章亦未寄给李老看,是他后来在报刊上看到的,写诗寄来则是二零零四年(甲申)的事了。 二零零七年初朱纯去世,有哀启告知亲友,李老收到后立即寄来了挽诗: 患难夫妻难问天,贱民生活史无前。 鲋鱼涸辙相濡沫,同德同心是宿缘。 上款“朱纯同志乡贤千古”,下款“九十叟李锐敬挽”,随后又托朱正兄带来了纪念文章,曾在《芳草地上》公开发表。 我自幼体弱,怯于出行,至今只进京四次,并未与李老谈过朱纯的事。朱纯更只去看过一次他,李老和张大姐为她特设家宴,请来京中旧时相识的女同志贺富明等作陪。席间他对朱纯说:“钟叔河坐牢九年受了苦,你受的苦比他还多,朱正和柳思都这样说的,还把你做木模工养活几个小孩、凭本事做到了五级师傅的事也告诉我了。将你们夫妇这样率真、这样能干的人开除、劳改,害得骨肉分离,真是太不爱惜人才,太不应该了!”朱纯回来转述此言,仍然感动得流泪。 以上三诗,均已收入《李锐文集》第九卷《龙胆紫集》中,文字偶有不同,此处均依原件。 (13.12.29)摄影王平 念楼壁上之四: 钱钟书《山斋凉夜》诗 钟叔河(长沙) 孤萤没竹淡收光,雨后宵凉气挟霜。 细诉秋心虫语砌,冥传风态叶飘廊。 相看不厌无多月,且住为佳岂有乡。 如缶如瓜浑未识,数星飞落忽迷方。 “山斋凉夜旧什录呈叔河贤友雅属”,下钤图章“钱印钟书”“默存”。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封信: 叔河贤友如晤:除夕前了笔墨宿债,忆吾友与正兄曾索拙书,即写两纸,所录皆四十年前寓贵省时作诗也。正思寄奉,忽得尊函,摄影风度大佳,珍藏时时展玩,如见故人矣。内人畏写字请兄豁免。老翁既被役,老妇可从宽减乎,一笑。献岁有新,维身心康泰著述新富为颂。笔秃不成字,草此即颂俪祉。钱钟书敬上,杨绛同候,一月二日夜。 这“一月二日夜”是在八十年代初,那么“四十年前”正好是钱先生执教蓝田(今涟源)“国师”时。《国城》说,学校的规模不大,除了女学生和家眷,全都住在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这便是离蓝田镇不到半里的“李园”,也就是诗题中的“山斋”。 从来信看得出,我乞字的对象本是钱杨两先生。但钱先生宁愿自己在除夕前该放松休息时“被役”,也要替杨先生请求“豁免”。联想起诗中“细诉秋心”“岂有乡”的离人寂寞,这一对青春作伴白首同归的文人夫妇之伉俪情怀,确实令人忻羡。 钱杨的学问文章早由历史定位,完全不必再以书名;但我对两先生的书法,也和对他们的文章一样喜欢。署“钱钟书默存稿,杨绛季康录”的影印本《槐聚诗存》,至今常在我案头枕畔。书中一九四零年部分第二十九页下的《山斋凉夜》,和写给我的有两字不同,即首联中“没”字作“隐”,“挟”字作“蕴”,再就是末联中“如缶如瓜”有小注:“流星如缶如瓜云云,见后汉书天文志。”由杨先生秀雅的楷法写出来,和钱先生行云流水的手迹对观,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真是“四美具,二难并”了(“四美”谓两先生的文辞和书法,因为书中也有钱氏手迹和杨的文章)。 现在该说到“李园”和“国师”了。予生也晚,抗战胜利前足迹不出长沙和平江,未曾游涉李园,对国师却还有过一点点关系。大姐一九四零年前后读书安化桥头河,去蓝田不远,订阅了那里印行的《学与思》杂志,上面常见出自国师的文字。有篇记师生联欢,写到“父子教授”同时出席而态度迥异,年轻的那位语出惊人,丰采超群,着西装还打了根红领带。小学生的我对教授的名字不怎么关心,却记住了那根红领带。 第二年进了初中,“英文先生”是国师的毕业生,曾在课堂上讲过他的老师和太老师,一个英文系主任一个国文系主任,学问都非常之了不起,太老师却好像更偏爱自己的小女婿(也是国文系的老师)。这些故事学生们听过也就听过了,几个顽皮点的甚至还敢低头议论,“吹老师还不是吹他自己”。但因为红领带印象深刻,所以先生眉飞色舞的样子亦未能忘。 及年岁稍长,读过《围城》和《谈艺录》,又读了从王闿运讲到徐志摩的《现代文学史》,知道了“父子教授”的详情,理性上和感性上自然而然地认同和倾倒于钟书先生。八十年代编《走向世界丛书》,得到钟书先生青及,给予指导,对他就更加感激了。有次我和先生闲谈,谈到国师学生在湖南教书的很多,我自己就当过一个学期他学生的学生,却说不出那位“英文先生”的名字。他给我写《山斋凉夜》,称我“贤友”,可能也与这一谈有关,我以为。 就在这前后不久,某大学准备开“钱基博学术讨论会”,着手整理出版钱氏的全集。据说钟书先生对此不甚热心,表示反对“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讲谈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引起议论。我向钟书先生问及此事,他回信说: ……先君遗著有独绝处,然出版尚非其时。其弟子辈尊师而无识力,急于刊行;弟于此事不敢置可否,蒙不孝之讥而已…… 话说得很清楚,他不仅没有否定老先生的学术贡献,还肯定了其“有独绝处”也就是有学术价值,担心的只是“弟子辈无识力”,不能将其整理出版好。我不识相,却打电话去,说我虽然也无识力,但身在湖南,老先生在蓝田时印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六十四开土纸本是认真读过的,认为它确实“有独绝处”,还是想在湖南将其和李肖聃《湘学略》合为一册印行,请求允许。他笑答:“我这里只能一视同仁。湖南想印,就去找我的妹妹吧。” 于是我便去找了钟霞先生。她很快便授权了,并且写来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后记,最后几句是:“本书初版在蓝田印成……我一直珍藏着,文革初期它被当作“四旧”销毁了……岳麓书社居然寻得了一个初版本,重新付印,让父亲的遗著得与世人见面,我很感谢。四十多年前我作过校对,现在又作一次校对,使我沉浸于回忆中。寒风之夜,李园四周,万壑松涛在响。西侧一室,橘黄的灯焰摇晃着,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四十多年了。”落款是“钱钟霞校读后记,一九八五年元月于武昌”。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到底是钱钟书的妹妹啊! 图片说明: 1.钱钟书赠钟叔河《山斋凉夜》诗(摄影:王平) 2.钱钟书致钟叔河信(摄影:王平)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系创刊于年的《文艺生活》杂志系列刊物之一,全国公开发行,每月1日出版;大16开彩印,每期9印张页码。国际标准刊号:ISSN—,国内统一刊号:CN43-/I,邮发代号:42-6,定价:29元/期,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文艺生话·艺术中国》以书画、收藏为主打方向,设有“书画精赏”“大家”“名家”“文房清玩”“非遗之窗”“名家推崇”“兰亭梅谱”“艺坛新彦”“艺林漫谈”“理论研讨”“院校风采”“艺苑方阵”“光影艺术”“来稿选登”等等栏目,举凡古今书画大家的艺术研究、精品赏析的稿件都是本刊热诚期盼的。作品采用后,寄送稿酬和祥刊。 电子信箱:hnyszg@.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zy/7332.html
- 上一篇文章: 性别比例不是11的生物举例
- 下一篇文章: 建议向向阳花看齐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