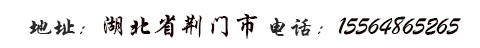爱默森梭罗的一生下
|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RalphWaldoEmerson,-),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爱默森①关于个人的理论是他的思想的基本,而他最好的作品却写的是个别人物。他对于梭罗的一篇素描,那神韵使人无法模仿;这一篇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摘出的,爱默森在日记中描写他和那比他年轻些的朋友的多次散步,那友人是一个自然学家,同时也是个哲学家;然而它也是根据回忆写出的,同时也出于真挚的感情——他在梭罗的墓前感觉到大地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心灵。他知道怎样用梭罗自己的话来表现他。怎样引用别人的语句,这是一种艺术,而从来没有人将这一点像爱默森在这里表示得这样清晰。——张爱玲 与他一同散步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一种特权。他像一只狐狸或是鸟一样地彻底知道这地方,也像它们一样,有他自己的小路,可以自由通过。他可以看出雪中或是地上的每一道足迹,知道哪一种生物在他之前走过这条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向导员必须绝对服从,而这是非常值得的。他挟着一本旧乐谱,可以把植物压在书里;他口袋里带着他的日记簿与铅笔,一只小望远镜预备看鸟,一只显微镜,大型的折刀,麻线。他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坚固的皮鞋,坚牢的灰色裤子,可以冒险通过矮橡树与牛尾菜,也可以爬到树上去找鹰巢或是松鼠巢。他徒步涉过池塘去找水生植物,他强壮的腿也是他盔甲中重要的一部。我所说的那一天,他去找龙胆花,看见它在那宽阔的池塘对过,他检验那小花之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把日记簿掏出来,读出一切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他的票据几时到期。兰花要到明天才开花。他想他如果从昏睡中醒来,在这沼泽里,他可以从植物上看出是几月几日,不会算错在两天之外。红尾鸟到处飞着;不久那优美的蜡嘴鸟也出现了,它那鲜艳的猩红色非常刺眼,“使一个冒失地看它的人不得不拭眼睛”,它的声音优美清脆,梭罗将它比作一只医好了沙哑喉咙的莺。不久他听到一种啼声,他称那种鸟为“夜鸣鸟”,他始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鸟,寻找了它十二年,每次他又看见它,它总是正在向一棵树或是矮丛中钻去,再也找不到它;只有这种鸟白昼与夜间同样地歌唱。我告诉他要当心,万一找到了它,把它记录下来,生命也许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给他看的了。他说,“你半生一直寻找着而找不到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和它觌面相逢,得窥全豹。你寻它像寻梦一样,而你一找到它,就成了它的俘虏。”梭罗湖畔的小屋 他对于花或鸟的兴趣蕴藏在他心灵深处,与大自然有关——而他从来不去试着给大自然的意义下定义。他不肯把他观察所得的回忆录贡献给自然史学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将那描写单独拆下来,与我脑子里别的与它有关的东西分开,在我看来,它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与价值:而他们并不要那些附属的东西。”他的观察力仿佛表示他在五官之外还有别的知觉。他看起东西来就像用显微镜一样,听起声音来就像用聚声筒一样,而他的记忆力简直就是他所有的见闻的一本摄影记录。然而,没有人比他更知道这一点: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实给你心灵的印象,或是对于你心灵的影响。每一件事实都光荣地躺在他心灵里,代表整个结构的井井有条与美丽。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条猎犬或是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约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学与鱼类学,用这温和的方式打猎。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汤麦斯·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蛇盘在他腿上;鱼游到他手中,他把它们从水里拿出来;他抓住山拨鼠的尾巴,把它从洞里拉出来;他保护狐狸不被猎人伤害。我们这自然学家绝对慷慨;他什么都不瞒人:他肯带你到苍鹭常去的地方,甚至于到他最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那里——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再会找到那地方,然而无论如何,他是愿意冒这个险的。从来没有任何大学要给他一张文凭,或是要请他去做教授;没有一个学院请他做它的特约撰述员,它的考察家,或是仅只做它的一个会员。也许这些饱学的团体怕被他讽刺。然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深知大自然的秘密与天才;这种知识的综合,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广大更严正。因为他毫不尊敬任何人任何团体的意见,而只向真理本身致敬;他每逢发现一个学者有重视礼貌的倾向,就不信任这人了。他本城的居民起初只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后来渐渐地尊敬钦佩他,雇他测量的农民很快地就发现他稀有的精确与技巧,他熟知他们的田地、树木、鸟类、印第安人的遗迹与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使他能够告诉他们许多事,关于他们的农场,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所以他们开始有点觉得仿佛梭罗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他们的田地。他们也觉得他的个性的优越性,这使他对于一切说话都有分量。康柯德有许多印第安人的遗物——箭镞、石凿、杵,与陶器的碎片;在河岸上,大堆的蚌壳与灰是一种标志,表示那是野蛮人常去的地点。这些,与每一件与印第安人有关的事,在他眼中都是重要的。他到缅因州去游历,主要是为了爱印第安人。他可以看到他们制造树皮独木舟,同时,还可以一试身手,在湍流上操舟。关于怎样制造石箭镞极想研究;他临终的时候还嘱咐一个动身到落矶山去的青年,叫他找一个知道怎样制造石箭镞的印第安人:“为了学到这个,值得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次。”偶尔有一小队潘诺布斯葛忒印第安人到康柯德来,夏天在河岸上搭起帐篷,住几个星期他总要和他们之间最好的一些人结交。他最后一次到缅因州游历,老城的一个聪敏的印第安人,名叫约瑟·波利斯,做他的向导做了好几个星期,他从这人那里得到很大的满足。他也同样地对每一件天然的事实都感到兴趣。他深入的观察力在整个的自然界中都发现同样的法律,据我所知,没有另一个天才能像他这样迅速地从一个单独的事实上推知普遍的定律。他不是只知道研究某一种部门学问的腐儒。他张开了眼睛接受美,耳朵随时接受音乐。他不是仅只在稀有的情形下才找到美与音乐,而是无论到哪里都找到。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在单独的曲调中;他在电报线的嗡嗡声中也发现诗意的暗示。他的诗有好有坏;无疑地,他缺乏一种抒情的能力与文字技巧,但是他在他性灵的知觉上有诗的泉源。他是一个好的读者与批评家,他对于诗的判断是基本性的。任何作品中有没有诗的原素,是瞒不过他的;他渴望得到诗的原素,这使他不注意浮面的美,也许还藐视它。他会撇开许多细致的韵节,而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出每一段或是每一行活的诗;他也善于在散文中找出同样的诗意的魅力。他太爱精神上的美,所以相形之下,对于一切实际上写出来的诗都没有多大敬意。他钦佩易斯契勒斯②与萍达;但是,有一次,有人在那里赞美他们,他却说易斯契勒斯与别的希腊诗人描写阿波罗与奥菲斯,从来没有一段真的诗,或者可以说没有好的诗。“他们不应当一味缠绵悱恻,连木石都被感动了;而应当向诸神唱出那样一首赞美诗,唱得他们脑子里旧的思想统统排斥出来,新的吸收进去。”他自己的诗章往往是粗陋有缺点的。金子还不是纯金,而是粗糙的,有许多渣滓。百里香与玛菊伦花还没有酿成蜜。但是他如果缺少抒情的精美与技巧上的优点,如果他没有诗人的气质,他从不缺乏那启发诗歌的思想,这表示他的天才胜过他的才能。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他喜欢每一个思想都化为一种象征。你所说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它的印象有价值。因为这缘故,他的仪表是诗意的,永远惹起别人的好奇心,要想更进一层知道他心灵的秘密。他在许多事上都是有保留的,有些事物,在他自己看来依旧是神圣的,他不愿让俗眼看到,他很会将他的经验罩上一层诗意的纱幕。凡是读到《瓦尔登湖》这本书的人,都曾记得他怎样用一种神话的格式记录他的失望——瓦尔登湖 “我很久以前失去一条猎犬,一匹栗色的马与一只斑鸠,至今仍旧在找寻它们。我向许多游历的人说到它们,描写它们的足迹,怎样唤它们,它们就会应声而至。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那猎犬的吠声,与马蹄声,甚至于曾经看到那斑鸠在云中消失;他们也急于要寻回它们,就像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一样。”他的谜语是值得读的。我说老实话,有时候我不懂他的辞句,然而那辞句仍旧是恰当的。他的真理这样丰富,他不犯着去堆砌空洞的字句。他题为《同情》的一首诗显露禁欲主义的重重钢甲下的温情,与它激发的理智的技巧。他古典式的诗《烟》使人想起西蒙尼地斯③而比西蒙尼地斯的任何一首诗都好。他的传记就在他的诗里。他惯常的思想使他所有的诗都成为赞美诗,颂扬一切原因的原因,颂扬将生命赋予他并且控制他的精神的圣灵——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尤其是在这宗教性的诗里——其实现在就是我诞生的时辰,也只有现在是我的壮年;我决不怀疑那默默无言的爱情,那不是我的身价或我的贫乏所买得来,我年轻它向我追求,老了它还向我追求,它领导我,把我带到今天这夜间。虽然他的作品里说到教会与牧师有时候语气很暴躁,他是一个稀有的温柔的绝对信奉宗教的人,无论在动作或是思想上,他都绝对不会亵渎上帝。当然,他独创一格的思想与生活使他孤立,与社会上的宗教形式隔离。我们不必批评他这一点,也不必认为遗憾。亚里斯多德早已解释过,说,“一个人的德性超过他那城市中其他的公民,他就不复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了。他们的法律不是为他而设的,因为他对于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律。”梭罗是最真挚的;先知们深信道德的定律,他圣洁的生活可以证明他们这种信仰是有根据的。他的生活是一种肯定的经验,我们无法忽视它。他说的话都是真理,他可以作最深奥最严格的谈话;他能医治任何灵魂的创伤;他是一个友人,他不但知道友谊的秘密,而且有几个人几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将他奉为先知,知道他那性灵与伟大的心的深奥的价值。他认为没有宗教或是某种信仰,永远做不出任何伟大的事;他认为那些偏执的宗派信徒也应当牢记这一点。当然,他的美德有时候太趋极端。他要求一切人都绝对诚实,毫不通融,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这是他那种严肃的态度的起因,而这严肃的态度使他非常孤独,他虽然是自愿做隐士,却并不想孤独到这一个地步。他自己是绝对正直的,他对别人也要求得一样多。他憎嫌罪恶,无论什么荣华富贵也不能掩盖罪恶。庄严的富有的人们如果有欺骗的行为,也最容易被他看出来,就像他看见乞丐行骗一样,他对他们也同样地感到鄙夷。他以这样一种危险性的坦白态度处事,钦佩他的人称他为“那可怕的梭罗”,仿佛他静默的时候也在说话,走开之后也还在场。我想他的理想太严格了,它甚至干涉他的行动,使他不能够在人间得到足够的友情,这是不健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总惯于发现事物与它们的外表相反,这使他有一种倾向,总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他那种敌意成了一种习惯,这习惯毁伤了他早期的作品的外貌——那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手法,就连他后来的作品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作风,以一个完全相反的字眼或思想来代替那通常的字眼或思想。他赞美荒山与冬天的树林,说它们有一种家庭气氛,发现冰雪是闷热的,称赞荒野,说它像罗马与巴黎。“它这样干燥,你简直可以叫它潮湿。”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眼前的一个物件或是几个综合的物件,他要在那里面看出一切自然界的定律。有些人没有哲学家的观察力,看不出一切事物的一致性;在他们眼光中,他这种倾向当然是可笑的。在他看来,根本无所谓大小。池塘是一个小海洋;大西洋是一个大的华尔敦池塘。每一件小事实,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虽然他的原意是要公正,他似乎有一种思想萦绕于心,以为当代的科学自命它是完美的,而他刚正发现那些有名的科学家忽略了某一点,没有鉴别某一种植物种类,没有描写它的种子,或是数它的花萼。我们这样回答他,“那就是说,那些傻瓜不是生在康柯德;但是谁说他们是生在这里的?他们太不幸了,生在伦敦,或是巴黎,或是罗马;但是,可怜,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他们很吃亏,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康柯德附近的培次门池塘,或是九亩角,或是贝琪·史多沼泽,而且,上天派你到这世界上来,不就是为了加上这点观察?”他的天才如果仅只是沉思性的,他是适于这种生活的;但是他这样精力旺盛,又有实际的能力,他仿佛天生应当创造大事业,应当发号施令;他失去了他稀有的行动力,我觉得非常遗憾,因此我不得不认为他没有壮志是他的一个缺点。他因为缺少壮志,他不为整个的美国设计一切,而做了一个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但是,这些弱点,不论是真的还是浮面上的,都很快地消失在这样健康智慧的一个性灵的不断的生长中,以它的新胜利涂没它的失败。他对于大自然的研究是他永远的光荣,使他的友人们充满了好奇心,想从他的观点看这世界,听他的冒险故事。他的故事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兴趣。他一方面嘲笑世俗的文雅习惯,然而他自己也有许多文雅的习惯。他怕听他自己的脚步声,砂砾轧轧作响;所以他从来不是自愿在路上走,而喜欢在草上、山上、树林中行走。他的知觉是敏锐的,他说晚上每一个住宅都发出恶气,像一个屠场一样。他喜欢苜蓿纯洁的香味。他对于某些植物特别有好感,尤其是睡莲;次之,就是龙胆、常春藤、永生花,与一棵菩提树,每年7月中旬它开花的时候他总去看它。他认为凭着香气比凭视觉来审查更为玄妙——更玄妙,也更可靠。当然,香气揭露了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捉摸不到的东西。他凭香味可以嗅出俗气来。他喜欢回声,说它几乎是他所听到的唯一的同类的声音。他酷爱大自然,在大自然中独处感到非常快乐,甚至于使他嫉视城市,城市的教化与谋略将人类与他们的住宅改变得不成模样。斧头永远在那里破坏他的树林。他说,“幸而他们不能把云砍下来。”“那蓝色的背景上用这纤维质的白色颜料画出各种形状。”我从他未发表的原稿上摘出几句话来,附在这里,不但可以作为他的思想与感情的纪录,而且也是为了它们的描写能力与文艺价值——有些“情况证据”是非常有力的,譬如有时候你在牛奶里发现一条鲟鱼。鲢鱼是一种柔软的鱼,滋味像煮熟的皮纸加上盐。年轻人收集材料,预备造一座桥通到月亮上,或是也许在地球上造一座宫殿或庙宇,而最后那中年人决定用这些材料造一间木屋。健康的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比吃糖还甜。我搁上一些长青树枝,那腴美辛辣的爆炸声在耳朵里听来,有芥末的感觉,又像是无数联队的枪炮声。枯树爱火。蓝鸟把天驮在它背上。莺在绿色的枝叶中飞过,仿佛它会使树叶着火。长生不老的水,连表面都是活的。火是最不讨厌的第三者。羊齿草纯是叶子,大自然制造它,是为了要给我们看它能造出多么好的叶子。没有一种树有像山毛榉那样美丽的树干,那样漂亮的脚背。那淡水蚌,埋在我们黑暗的河底的泥里,它壳上美丽的虹彩是从哪里来的?如果那婴儿的鞋子是另一个小孩的旧鞋,那真是一个艰苦的时代了。我们什么都不必怕,只怕恐怖。相形之下,上帝或者宁取无神论。你能够忘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稍稍需要一点思想,用它作为全世界的庙祝,照管庙宇中一切宝贵的物件。我们没有经过品性上的播种时期,怎么能预期思想上有收获?有期望而镇静处之,不动声色,只有这种人,我们能够将宝贵的礼物付托在他们手里。我要求被溶化。金属品在火中溶化,你只能要求它对火温柔。它不能对任何别的东西温柔。梭罗之墓 植物学者知道有一种花——我们那种夏季植物,叫做“永生花”的,与它同是“菊科”——生在提乐尔山上的危崖上,几乎连羚羊都不敢上去,猎人被它的美引诱着,又被他的爱情引诱着(因为瑞士姑娘们非常珍视这种花),爬上去采它,有时候被人发现他跌死在山脚下,手里拿着这朵花。植物学家叫它薄雪草,但是瑞士人叫它Edelweiss,它的意义就是“纯洁”。我觉得梭罗仿佛一生都希望能采到这植物,它理应是他的。他进行的研究,规模非常大,需要有极长的寿命才能完成,所以我们完全没想到他会忽然逝世。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了,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侪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应当和最高贵的灵魂作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学完了这世界上一切的才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①爱默森,又译作爱默生。 ②Aeschylus(公元前-),古希腊悲剧诗人。 ③Simonides,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希腊抒情诗人。 选自《爱默森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2月出版 作者 [美]爱默森 译者 张爱玲 配图 源自网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ongdana.com/ldjj/7502.html
- 上一篇文章: 藏医药在世界专题介绍
- 下一篇文章: 神奇藏医药专题刚刚一个月大